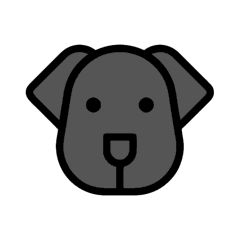《漂》
连载中原创现实’25 征文比赛
# 漂
文/人仿
迷宫。
从公交车上下来,还没来得及把抱在怀里的旧书包背到背上,这个词就立马占据了她的脑海。
上海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道路在她眼前向远方无限延伸,缠绕在一起的高架桥令她头晕目眩,挤着向上生长的高楼将她的视野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她抬头看向天空,几座摩天大楼钢钎般地从视野边缘刺入,把天空像过年杀猪一样捆绑在人类工业的架子上。
这个连交通都要地上地下分成三层才堪堪够用的拥挤城市,让她感到无所适从。在她的想象中,上海应该和她上高中的县城差不多,只是面积会更大,人会更多,而不应该是这样地让人感到——她想了几秒,才皱着眉头从词汇库里挑出一个词——迷失。
她下意识地用脚搓了搓地面,湿漉漉,冷冰冰,硬邦邦,让她开始怀念起农村老家那让人感到亲切的泥土地。天空中飘着小雨,她看到一片细嫩的叶子从树上被冲刷下来,漂在路边的积水上,顺着水流坠入井盖。
随后,她环顾四周, 看到了灯,无数的,无穷无尽的灯——路灯、红绿灯、流动的车灯、路人的智能手机、霓虹招牌、写字楼的内透、巨大的电子广告屏、建筑的LED外立面……铺天盖地,堆叠在一起,没有一丝缝隙。
按照老家的习惯,在天黑得让万物都模糊成灰黑色的一团雾之前,村里的人们是不会点灯的。而现在天光只是微暗,尚可让她看清自己那双穿了三年的运动鞋上,鞋头那处开胶的豁口。她本能地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怪异,认知失调引起一种迷幻感,仿佛整个城市都是虚幻的,是一场浮在梦里的海市蜃楼。
她满满地吸了一口气,潜进五光十色的街道,拨开迎面而来的人群,向城市深处游去。最开始,她并不敢向两旁张望,只憋着气往前走。后来,她稍微适应了一点,心里的陌生感不是那么强烈了,周围的水也不再那么冰凉。于是她敢于慢慢睁开眼睛,用眼角余光,小心翼翼地刮取一些周边的景色,放进脑海里咀嚼、研磨,试探着将那些新奇的事物,同她旧有的经验建立连接,用她朴素的感觉,尝试去理解这座比她所去过的最繁华的县城,还要先进三十年以上的巨型城市的,冰山一角。
天色渐晚,等她一边问路,一边从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的楼宇间,钻行到要报道的学校时,却被告知各院安排接待新生报到的人都已经收摊了,她只能明天白天再来报道。
她茫然无措地徘徊在校园门口,背上的书包一下子变得沉重,坠得她难受。其实里面的东西并不多:几件穿的很旧的夏季衣服,一双帆布鞋,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以及那一沓她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、包在红布里的彩礼钱。虽然书包不重,但她已经在20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上消磨尽了体力,又坐了一小时公交车,走了这么多路,身体中再也榨不出一丝剩余的精力。
人一旦在路上漂泊久了,脑子里就会只剩下一个想法,就是赶紧找个安定的地方休息。
在近乎本能的对安定的渴望的驱使下,她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,路过一片老旧小区时,她被刺眼的霓虹招牌吸引住了。“宾馆”两个大字变换着红绿蓝三色,刺向她的视神经,撩拨着她摇摇欲坠的心灵。她被迷住了一般,迈着漂浮的步子,拐进了那个招牌所指的铁防盗门。
门厅里,一个胖女人堆在柜台后面的躺椅里,盯着手机屏幕,麻木地大笑。
她站在门口观察了一会胖女人的智能手机,摸摸自己口袋里的按键式老年机,然后咬咬牙,走过去,问:“多少钱一晚?”
对方头也没抬:“你要单人间还是标间。”
“最便宜的多少钱呢?”
“七十。”
她拉开书包,从那一沓用红绳捆着的票子中,郑重地抽出一张,放在柜台上。胖女人拈起来,对着电脑屏幕照照,又把它塞进验钞机。
“这是真币。”验钞机突然叫起来,把她吓了一跳。
胖女人拉开抽屉,找了三张皱巴巴的十块回来,接着拿起墙上挂着的钥匙,招呼匆忙把钱塞进兜里的她跟着走。
打开门,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架子床,一张塑料凳子,以及一个充当桌子的床头柜。她走进去,关上门,落满灰尘的荧光灯苟延残喘地洒下发紫的白光,昏昏沉沉地俯视着下面六平米的空间。
她脱掉鞋子,躺到床上,竭力伸展四肢。这已经很好了,起码它不会晃动,不会咣当作响,而且还能让她躺平,不用蜷缩手脚。 她下意识地抚摸书包的肩带,这个书包她从初中就开始背,六年间,肩带根部断了四次,又缝了四次,但其他部分始终坚挺。
恍惚间,她陷入了一种充斥着安定感的幻觉,她觉得自己的旅途已经抵达了终点,而身下这张床就是她最终的归宿——她不用再漂泊了。或许等到明天早上,她将会在美梦破碎的悲哀中醒来,并不得不继续面对残忍的现实。但至少今晚,她暂时获得了安宁。
疲惫涌了上来,她连灯都没关,就陷入了昏睡。
黑暗中,她梦到了从老家逃出来之前的时光。
第2节
文/人仿
1
迷宫。
从公交车上下来,还没来得及把抱在怀里的旧书包背到背上,这个词就立马占据了她的脑海。
上海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道路在她眼前向远方无限延伸,缠绕在一起的高架桥令她头晕目眩,挤着向上生长的高楼将她的视野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她抬头看向天空,几座摩天大楼钢钎般地从视野边缘刺入,把天空像过年杀猪一样捆绑在人类工业的架子上。
这个连交通都要地上地下分成三层才堪堪够用的拥挤城市,让她感到无所适从。在她的想象中,上海应该和她上高中的县城差不多,只是面积会更大,人会更多,而不应该是这样地让人感到——她想了几秒,才皱着眉头从词汇库里挑出一个词——迷失。
她下意识地用脚搓了搓地面,湿漉漉,冷冰冰,硬邦邦,让她开始怀念起农村老家那让人感到亲切的泥土地。天空中飘着小雨,她看到一片细嫩的叶子从树上被冲刷下来,漂在路边的积水上,顺着水流坠入井盖。
随后,她环顾四周, 看到了灯,无数的,无穷无尽的灯——路灯、红绿灯、流动的车灯、路人的智能手机、霓虹招牌、写字楼的内透、巨大的电子广告屏、建筑的LED外立面……铺天盖地,堆叠在一起,没有一丝缝隙。
按照老家的习惯,在天黑得让万物都模糊成灰黑色的一团雾之前,村里的人们是不会点灯的。而现在天光只是微暗,尚可让她看清自己那双穿了三年的运动鞋上,鞋头那处开胶的豁口。她本能地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怪异,认知失调引起一种迷幻感,仿佛整个城市都是虚幻的,是一场浮在梦里的海市蜃楼。
她满满地吸了一口气,潜进五光十色的街道,拨开迎面而来的人群,向城市深处游去。最开始,她并不敢向两旁张望,只憋着气往前走。后来,她稍微适应了一点,心里的陌生感不是那么强烈了,周围的水也不再那么冰凉。于是她敢于慢慢睁开眼睛,用眼角余光,小心翼翼地刮取一些周边的景色,放进脑海里咀嚼、研磨,试探着将那些新奇的事物,同她旧有的经验建立连接,用她朴素的感觉,尝试去理解这座比她所去过的最繁华的县城,还要先进三十年以上的巨型城市的,冰山一角。
天色渐晚,等她一边问路,一边从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的楼宇间,钻行到要报道的学校时,却被告知各院安排接待新生报到的人都已经收摊了,她只能明天白天再来报道。
她茫然无措地徘徊在校园门口,背上的书包一下子变得沉重,坠得她难受。其实里面的东西并不多:几件穿的很旧的夏季衣服,一双帆布鞋,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以及那一沓她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、包在红布里的彩礼钱。虽然书包不重,但她已经在20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上消磨尽了体力,又坐了一小时公交车,走了这么多路,身体中再也榨不出一丝剩余的精力。
人一旦在路上漂泊久了,脑子里就会只剩下一个想法,就是赶紧找个安定的地方休息。
在近乎本能的对安定的渴望的驱使下,她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,路过一片老旧小区时,她被刺眼的霓虹招牌吸引住了。“宾馆”两个大字变换着红绿蓝三色,刺向她的视神经,撩拨着她摇摇欲坠的心灵。她被迷住了一般,迈着漂浮的步子,拐进了那个招牌所指的铁防盗门。
门厅里,一个胖女人堆在柜台后面的躺椅里,盯着手机屏幕,麻木地大笑。
她站在门口观察了一会胖女人的智能手机,摸摸自己口袋里的按键式老年机,然后咬咬牙,走过去,问:“多少钱一晚?”
对方头也没抬:“你要单人间还是标间。”
“最便宜的多少钱呢?”
“七十。”
她拉开书包,从那一沓用红绳捆着的票子中,郑重地抽出一张,放在柜台上。胖女人拈起来,对着电脑屏幕照照,又把它塞进验钞机。
“这是真币。”验钞机突然叫起来,把她吓了一跳。
胖女人拉开抽屉,找了三张皱巴巴的十块回来,接着拿起墙上挂着的钥匙,招呼匆忙把钱塞进兜里的她跟着走。
打开门,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架子床,一张塑料凳子,以及一个充当桌子的床头柜。她走进去,关上门,落满灰尘的荧光灯苟延残喘地洒下发紫的白光,昏昏沉沉地俯视着下面六平米的空间。
她脱掉鞋子,躺到床上,竭力伸展四肢。这已经很好了,起码它不会晃动,不会咣当作响,而且还能让她躺平,不用蜷缩手脚。 她下意识地抚摸书包的肩带,这个书包她从初中就开始背,六年间,肩带根部断了四次,又缝了四次,但其他部分始终坚挺。
恍惚间,她陷入了一种充斥着安定感的幻觉,她觉得自己的旅途已经抵达了终点,而身下这张床就是她最终的归宿——她不用再漂泊了。或许等到明天早上,她将会在美梦破碎的悲哀中醒来,并不得不继续面对残忍的现实。但至少今晚,她暂时获得了安宁。
疲惫涌了上来,她连灯都没关,就陷入了昏睡。
黑暗中,她梦到了从老家逃出来之前的时光。
第2节
支持!特别期待
你好,已经20个小时没更新了。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休息。
迷妹催更!一天一章不过分吧猫老师ovo
2
郭志野的名字是在她的性别尚不为父母所知时,就由她父亲起好的。
当时她的哥哥刚刚考上县里的高中,大有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的架势,然后村西头的赤脚医生老刘头又信誓旦旦地指着她母亲的大肚子,说里面装的绝对是个儿子。于是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之中,她的父亲想了一宿,想出来“志野”这么个名字。这个一辈子没走出农村的男人,在连续的喜讯之下,盲目乐观地希望自己的二儿子可以有志气、有野心,和大儿子一起,接替他完成他所办不到的事——带一家人走出农村。
一个月后,郭志野的父母明白了两件事:一是职高虽然是“高中”,但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种“高中”,他们的大儿子大概率没法成为大学生;二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不可信,因为郭志野的母亲冒着高龄生产的风险,诞下了郭志野,而郭志野是个女孩。
这两件被父母日夜念叨的事情,产生了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,但十分沉重的压力,仿佛郭志野生来就该为这两件事偿还些什么。它们像影子一样跟着郭志野,环抱着她的童年,铁处女般地,用锐利的刺,从生活的各个角落轻轻戳刺她。对于这种戳刺到底在何时停止这个问题,郭志野设想过很多个时间点:在她每学期往家里拿回三好学生的奖状时,在她考上一所真正的普通高中时,在她高考查分过了一本线时……可是戳刺没有停止,一次也没有。
在被不断戳刺的过程中,郭志野渐渐明白,戳刺是永无止境的,因为这刺其实不是刺向她的,而是刺向父母的,只不过对于他们来说,生活的重担已经足够沉重了,再加上戳刺,就实在难以承受,因此他们不得不把痛苦向她转移一部分。
梦里,郭志野坐在村口,看村里各家的女人们,骑着电动车,叽叽喳喳地往村外走。她们要给在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饭,然后再回家继续照顾家里的小孩——有冒风险高龄生下的,也有在外务工的子女丢给他们的。
她看着她的母亲拎着新做的饭菜出去,过了许久,又拎着剩饭,和各家归来的女人们一起,出现在村外的土路上。她的母亲跟着那些女人一起,匆匆忙忙地掠过她,往各自的家里赶。没有人看向她,也没有人注意到她,她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女人一样,没有人能看到,在世界上并不存在。
但有一种情况例外,就是当她脱下臃肿的高中校服,换上初中时买的那件小吊带和牛仔短裤(都已经有些紧了,但还是能穿),走在村子中央的洋灰路上,从那些男人们面前经过的时候。只有这个时候,她才突然从世界上突然刷新出来,受到四面八方刺过来的注视。
那些男人们的目光黏在她身上,像触手一样,摸索、舔舐,留下粘稠的液体。她悄悄观察那些男人的眼神,里面充斥着贪婪、压抑、渴望,甚至还有乞求——不是乞求她,而是乞求老天爷,能把她一片一片地切开来,分给他们,好让他们囫囵吞下,填饱他们的欲望。
她常听到男人们在酒桌上说,女人的逼是空虚的,需要让男人去填满。但她觉得,比起她下身的那道缝隙,男人的心更像是他们口中的逼,因为男人的心总是嗷嗷叫着饿,撒泼打滚地,道德败坏地,逼迫他们把女人(大部分时候还得是漂亮女人)塞进它们的最深处,才能满足地打个饱嗝,偃旗息鼓。
她踩着众多男人用目光编织的红毯,路过两旁带院子的砖砌平房,一座又一座。那些院子的大门敞开着,但是她本能地知道她不能进去,因为那不是她的家。院子门口都坐着人,除了直勾勾盯着她看的男人,还有女人——那些男人的老婆。她们看向她的眼神,既挑衅又胆怯,既审视又嫉妒,既嘲笑又自卑。她是她们脑海中的假想敌,口中的不要脸的小婊子,以及心中的渴望成为的样子。
一种想要寻找什么的空虚感在梦里缠绕着她,她走了不知多少路,只为找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小院。它不用在外观或材质上与其他院子有什么区别,它只需要是她的家。但她没有找到,一直到她走到村子尽头,看到村口那条大路,也没找到她的家到底在哪。
当她打算掉头回去再找一遍时,她看到大路上开过来一辆大巴车,从上面下来一个处在青年和中年的交界处年纪的精瘦男人。那是她的哥哥。
郭志野对哥哥的印象很模糊,她开始记事的时候,哥哥就已经从职高毕业,去深圳打工了,鲜少回家。只有在每年过年的时候,才会拎着给她的礼物,先坐火车,再转大巴,最后出现在村口那条“村村通”工程新修的公路上。
哥哥冲她挥手,她跑过去,跟着哥哥一起,走了两步,就到了家里。她心里疑惑:为什么她死活寻找不到的家,哥哥就这么轻易找到了呢?
等她从疑惑中回过神来,她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平常吃饭用的那个低矮的小方桌上。四个人各占据方桌的一个边,她的对面是父亲,左手是母亲,右手是哥哥。他们三个都盯着她,上下打量,像是赶集时在肉摊上挑挑拣拣时,判断一块五花肉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。
“我还是感觉亏了,”父亲说,“咱家闺女这么漂亮,年纪也小,日后保准不愁嫁的。现在就这么嫁给老刘头家的大儿子,跟他家换了婚?”
“你光考虑闺女,那家里的小子你就不管了?”母亲打断道,“他都34了!要不是咱家闺女年纪小又漂亮,那老刘头舍得把他家22的闺女换过来做媳妇?”
郭志野低头看着自己紧紧攥着的手,硬卡纸做的录取通知书被她捏成了一个满是棱角的纸团。她在梦里感受不到手掌上的刺痛,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心痛。
“妹子,刘哥人不错的,虽然年龄差了几岁,但是你俩肯定能把日子过好的。”哥哥沉默了一会,最终还是开口了。
“你哥年纪大了,是时候寻个媳妇,要个孩子了,你得为延续香火的大事想想啊。而且那大学又远又花钱,不如早点嫁了,跟人好好过日子。”
郭志野没听出来这话是谁说的,传到她耳中的嗓音既像男声又像女声,既年老又年轻。她抬起头,默默看着那三个忽然变成陌生人的人,驱动着三张陌生的嘴,交错着张张合合,却发出同一个声音。她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哥哥就能很轻易地找到家:原来这里只是哥哥的家,并不是她的家。
那一夜,她偷偷从炕上爬起来,摸黑拿起书包,抓了几件衣服,拿了录取通知书,从炕洞里掏出老刘头家按照习俗送来的“年龄补偿费”,轻轻推开门,跑了出去。
星光下,郭志野向村外狂奔,速度快得像是要飞起来。她有志气,有野心,她要做哥哥没能力考上的那个,从童年起就一直戳刺她的,争气的大学生。
没想到还能吃到这样的饭!
这个开头完全是严肃文学了……😭
大佬教我写小说!
这个开头完全是严肃文学了……😭
大佬教我写小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