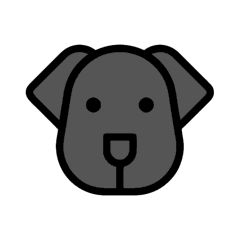【约稿】如氏的下午
短篇原创现实男虐男
感谢来自muttformaster的约稿。
这篇是父女主,其中有较为重口味的中年男s调教的场面,请谨慎阅读。
这篇是父女主,其中有较为重口味的中年男s调教的场面,请谨慎阅读。
# 如氏的下午
文/人仿
脖子上的布条勒得很紧。
他跪在玄关的鞋架旁,忐忑地等待着。不久之后就要回家的那一对父女,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,但他必须用最恭敬的方式,迎接他们回家。因为他们是他的主人。
七年前,跑长途货运的杜澎在沿着大车司机们口耳相传的路线,穿过一条村边被大车压烂的破路时,在村里的饭店看到有一个穿着破棉衣的老妇,挨桌问人要不要小男孩续香火。杜澎把老妇叫来细问,得知老妇的老伴早已去世,唯一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一起打工时,工地的电梯坠落导致双双死亡,她没办法再养活手里牵着的孙子,只能找个好人家托付出去。杜澎听完,当场便买下了那个八岁的小男孩。
按理说,凡是买男孩来续香火的人家,都会把买来的孩子视作己出,并让孩子继承本家的姓氏。但杜澎没有这样做,他并不在意所谓的香火,他在意的是他的女儿,杜如。十年前,她的妻子在为她诞下女儿时,难产大出血而死,杜如也因此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。因此,杜澎没有让买下的小男孩随自己的性,甚至没有给他起名,他只是想像旧社会一样,给家里买个伺候人的奴仆,顺便给杜如找个伴,补偿一下她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的伤痛。
这些事情,被亲奶奶卖掉的小男孩都不知道,那时候他还太小,理解不了也记不住这么复杂的事情。他脑海里最早的记忆,是第一次走进杜澎的家门,看到比自己大一岁的,漂亮的杜如姐姐时,心中的油然而生的欢喜和惊叹。
但是这种欢喜没能持续几秒。他记得当时,杜如叉着腰,高傲地跟他说,以后要管她叫“小主”,管杜澎叫“主子”。对于一个一直在农村生活,没有上过学,也没有看过电视的小男孩,是无法自主理解杜如从电视剧里看来的那些词汇是什么含义的,他只能木讷地点点头,心头的惊喜慢慢变成疑惑。
因为杜澎不让他姓杜,所以杜如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,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他做姓氏,从此他就顶着“如氏”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,开始了当牛做马的家奴生活。时间流转,到现在,杜如已经从小女孩变成了高二的青春少女,而如氏则在阴阳不良和长期饥饿中长成了瘦骨嶙峋的15岁少年。
轻快的脚步声打断了如氏的思绪,他连忙端正姿势,神思流过身上的每块肌肉、每个关节,确定它们输出了适量的力道,弯折成了规定的角度,这样才能维持最标准的伏地跪姿。但他其实有些过度担心,因为这跪姿是杜澎一点点用皮带“教”出来的,早已经刻进他的肌肉记忆,几乎不存在出错的可能。尽管杜澎自己其实是不知道他想要如氏怎么做的,他只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用皮带把如氏抽得皮开肉绽,缩在地上,失神地不断重复求饶的话。这种太监般的跪姿,是如氏一点点摸索出来,能让杜澎心里产生皇帝般的爽感,从而迅速消气的,好用的跪姿。
脚步声越来越近,杜家租的房子位于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事业单位的宿舍楼上,总共只有六层,没有电梯,杜家位于顶层。一般人连续爬到六层的时候,即使腿部肌肉不累,心态上也累了,脚步声往往都会变得沉重而响亮。因此如氏可以通过水泥台阶上传来的不同鞋子、不同力道、不同频率的踩踏声,判断出是谁来了。现在这种像小鹿一般,蜻蜓点水似的细碎快步,是杜如的。
钥匙在门外碰撞,插入锁孔,滞涩地扭转,随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咣啷咣啷地打开了。如氏抬头看去,一瞬间,杜如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,正对上如氏那双唯唯诺诺的,丫鬟般的眼睛。
如氏迅速移开眼神,低下头,看到杜如手里那张,被她用两个指尖轻巧地捏着的试卷。虽然卷面上的汉字他几乎完全看不懂,只能勉强地认出几个(还不确定有没有认错),但是上面的数字他是看得懂的——102,比之前拿回来的卷子上面的数字要低一些。
“啊,这是这次补习班模拟测验的卷子。”杜如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,眼神里有些害羞,也有些歉意。
如氏点点头。他其实不明白模拟测验到底是个什么概念,但从杜如的反应里,他能看出,这张画着各种符号的纸,和以前那些长得差不多的纸一样,都会让杜澎烦躁,从而给自己带来苦难,是颇为不详的东西。因此,出于对主人的话做出即时反应的义务,他只是点了点头,但并不能说出什么话来。
“你不用跟着伺候我了,”杜如转身往卧室走去,“你还是跪着等着迎接那个人吧,这样他回来心情好点儿,还能少骂我两句。”
随后,如氏卧室里响起书包被扔在床上的噗的声响,随后是电扇开关的喀哒声。时值七月中旬,北方进入雷阵雨多发的时节,积蓄了两天的厚重雨云笼罩着小城,水汽填满了空气分子的每一个缝隙,天候又闷又热,涨红了脸,憋着劲儿要来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骤雨。
家里并非没有空调,只是房东鸡贼地将空调另设了一个电表,收取额外的电费,因此杜澎和杜如都舍不得开,只一人有一个小电扇。如氏跪在门口,不知是汗还是潮气凝结成的水珠挂满了他的全身,周围静滞的空气压得他喘不上气,他听着杜如卧室里电扇的嗡嗡声,想象着那股风如果吹在自己身上,会是如何的畅快。
一阵突如其来的紧张感紧急中断了如氏的幻想。那是一种超前于意识和思考的恐慌,是身体在捕捉到最细微的线索时,来不及通知大脑,而先行让身体进入应激状态的脊髓反射。有人将这种机制称为直觉,也有人将这种感受认定是第六感,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。总之,在恐慌袭来的几百毫秒之后,如氏才弄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他听到了杜澎上楼的脚步声。
他的额头死死压在地面上,连呼吸和心跳都凝滞了。世界变得一片寂静,各种嘈杂的声音全部退潮般地离他远去,只有杜澎的脚步声,离他越来越近。
咚,咚,咚——
“贱奴给爸爸请安。”门推开的一瞬间,他重重磕头。
如氏口中所谓的“爸爸”,并非指的杜澎,而是指的杜澎的脚。这个“认足作父”的点子,是杜澎在听到同行轮班的司机,说起“有个外围为了挽回一个富二代竟然认富二代的狗做爹”的猎奇新闻时,忽然想到的。
直到杜澎坚硬的皮鞋底踩住他的后脑,如氏才停下来。他叼住皮鞋的后跟,一边含糊不清地念叨着“贱奴给爸爸更衣”,一边用嘴褪下鞋子。
一丝肉眼可见的白雾从皮鞋和脚的缝隙间蒸腾出来,那是长途出车,吃睡都在车上,连续三四天不曾脱鞋,而从脚底分泌出来,经过反复闷蒸、浓缩出的脚汗蒸汽,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的显现。浓重的恶臭逸散到空气中,被如氏吸入鼻腔,像强酸一样立刻腐蚀了他的嗅觉神经。极其浓郁的咸臭甚至让他感到一种浓重的苦涩,仿佛鼻腔和气管都被脚汗蒸汽夺取了水分,开始皱缩、枯萎。
“回来了?”杜如从卧室里钻出来,淡淡地打招呼。
“他妈的,今天卸货的时候手滑了一下,被接货的老板扣了五十卸货费。”杜澎一边骂,一边脚下发力,把如氏的头狠狠踩进鞋窝。
从四面八方,洪水似的涌来的臭味,立刻让如氏全身的肌肉都不自觉抽搐起来。即使嗅觉中枢立刻在恶臭中近乎麻痹,但杜澎作为多年的脚气患者,那种真菌发酵所产生的,超越嗅觉的,反人类的味道,直接侵染到他的骨髓、他的灵魂里,让他像被水淹没,快要淹死的人一样渴求新鲜的氧气。
杜澎没有在意如氏激烈的反应,他隔着袜子,把发痒的脚底踩在如氏留着寸头的头上,在脑上那些坚硬的发茬上摩擦。茁壮的发茬被迫穿透袜子纤维的缝隙,刮挠、戳刺着令人发痒的死皮,和恶心的溃烂处,让杜澎感到一阵舒适。
杜如皱了皱鼻子,退了两步,借口去摆碗筷,迈着小碎步溜去厨房里了。
“行了,一会吃饭的时候再好好伺候你爸爸。现在先给我把衣服换了。”杜澎命令道。
换完衣服,杜如已经摆好了碗筷。父女两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小的餐桌两侧,桌上挨挨挤挤地放着两副碗筷,以及杜澎买回来的吃食:两盒路边三轮车小摊上买的快餐炒菜,几个馒头,一小塑料袋炸花生米,以及一提罐装啤酒。桌下则是跪着的如氏,他艰难找着角度,用牙齿轻轻啃食杜澎脚底的死皮和腐肉,缓解他脚底的瘙痒。
“这几天都不出车吗?”杜如看着啤酒问, 平淡的语气仿佛她和杜澎只是同事关系。
“最近活儿少。”杜澎只是简单地回答。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脚底,如氏那湿润柔软的舌头和略显尖锐的牙齿,交替给他带来的轻抚和解痒的舒爽感受。
两个人都没再说话,客厅里一片寂静,只有杜澎的脚底板上,如氏用舌头像犁地一样来回刮蹭,用牙齿像锄头开垦一样地啃食,所发出的沙沙的声音。
过了二十分钟,直到如氏的舌头和咬肌都开始酸痛,桌上只剩下一点残留的菜汤,和两个被当成烟灰缸的空啤酒罐子,杜如才犹犹豫豫地开口,说:“模拟考的成绩下来了。”
“多少分?”
“反正是够本科了。”
“我问你多少分!”杜澎提高音量,他的脚趾狠狠抠紧如氏的脸,如氏感觉自己的五官都要被从脸上挖下来了。
“102……”杜如小声说。
“怎么又下降了!以前不是能考130的吗!”
“这次考的是高三难度的题!算了,跟你说了你也不懂!”杜如一撑桌子,站起来,大步走回自己的房间,砰地关上门。
“你!”杜澎起身,刚想去追,电话却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,随即坐了回去,抄起电话接通:“哎,王老师——”
他对着手机,满口答应,脸上都跟着不自地对着空气流露出紧张而讨好的笑容,也顾不上使用脚下的如氏了,只是僵僵地坐着,好像魂被吸到了电话的另一边。
“哎,哎,好的王老师,我理解,咱们都是为了孩子的成绩。您让我再考虑一下,后天孩子过去上课的时候,让她跟您说要不要报强化班。”
挂断电话,杜澎的脸迅速垮了下去,他烦躁地点开微信,忽略那一堆货运群里的未读消息,直接点开支付界面,看着上面堪堪达到五位数的数字,陷入纠结。
如氏也感受到了杜澎的焦虑,虽然是通过被杜澎踹脸的方式。杜澎沾满他口水的脚底,直直地踹在他的脸上,带着一股发泄的力道,几乎要把他的脸皮从骨头上搓下去。他被踹得东倒西歪,在地上栽倒又爬起,一遍遍重新跪到杜澎脚下,无言地履行着沙包的职责。
他宁愿自己多受点苦,也不愿意杜澎把气撒在杜如的身上。他已经形同枯槁,浑身布满了各种类型的伤疤,再承受多一些痛苦也无所谓。可是杜如,他的小主,她的身体是那样的富有青春活力,焕发着即将成年的少女特有地光彩。那吹弹可破的细腻皮肤,如何经得起杜澎的粗糙有力的大手的拍打?那小鹿一般的纯洁活泼的心灵,又如何经得起杜澎毫无文化,满口粗鄙之语的责骂?
杜澎从哈德门烟盒中抽出一支新的点上,猛吸了一口,一脚将如氏踹了个趔趄:“去把东西收拾了,然后把妞妞给我叫过来。”
如氏跪直,把空的泡沫盒子和啤酒罐等垃圾扫到垃圾袋里,叼着前往厨房扔掉。由于父女两个都不会做饭,也没时间学,因此厨房几乎未曾使用过,成了如氏的狗窝,兼堆放杂物的地方。在厨房,如氏举起快餐盒,喝掉了里面的菜汤。杜澎是不会买如氏的食物的,他对如氏的思路还停留在农村养狗的阶段,即给狗吃点人的剩饭就行了,没有剩饭就饿着。因此,如氏每天就只能靠菜汤里的油星补充一些能量。杜如上高中后,如氏的境遇才好一点,因为杜如会好心地托名减肥,给他剩几口馒头米饭,或是假装吃到了花椒或骨头渣子,吐出一口嚼碎的菜或肉留给他。
因此,如氏是十分喜欢杜如的,在他封闭的,全部面积只有60平米的世界里,杜如就是他的天使,他的女神。他爬到杜如的卧室门前,虔诚地叩首,轻声呼唤着“小主”。杜如还在赌气,房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,如氏只能听到客厅传来杜澎外放看短视频,隔几秒就会传来一次的猴子笑声。
直到如氏听着杜澎又抽完了两根烟(他通过两次打火机的声音判断的),他才终于听到门后面,啪嗒啪嗒向他走来的拖鞋声。
“干什么?”门缝里露出杜如的黑色猫猫拖鞋,她水润的脚趾蜷缩在鞋尖,白皙得刺眼。
“主子请您去客厅。”如氏卑微地伏在地上。
门打开了,他的头被柔软的拖鞋底狠狠踹了一脚,随后门又重重地关上。
如氏只能颤抖着爬回杜澎脚边,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杜澎的表情,恐惧地陷入对自己会遭到什么惩罚的猜想中。杜澎一手拿着手机,一手抓着如氏的头发,不由分说的把他的脸拽到自己裆下。那是他要撒尿的意思。
杜澎对排泄是没什么羞耻心的,他在长途货运的过程中,经常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排泄,不知被路过的司机和路人看过多少次了。他喜欢生殖器露在风中撒尿的感觉,但他更喜欢把它插进如氏的口腔,在温润柔软的包裹中一泻千里,顺便还能欣赏如氏强忍干呕的痛苦表情。所以他毫无羞耻地脱下裤子,往如氏胃里灌了一泡充满啤酒的代谢产物的,腥臊的浓尿。
浓重的骚味瞬间激发了如氏的生物本能,他的胃立刻就猛烈收缩起来,他的身体自然地想要抵抗入侵的污物,把尿液排出体外,但他的大脑却下达着相反的命令。在违抗天性的对抗中,如氏的五官扭曲成一团,腹部一凹一凹地向内抽搐,坚持了半分钟,才终于等到杜澎尿完,瘫在地上干呕着喘着粗气。
提上裤子,杜澎踩过如氏的腹部,大步走向杜如的房门,握起拳头猛砸。
“干什么!”杜如一把拉开门,站在门口和杜澎对峙。
杜澎的拳头举起又放下。无论再怎么生气,他也是没法对女儿下手的,他觉得亡妻的在天之灵还在注视着他,要他做一个好父亲。最终,他嗫嚅了几下,还是忍住了即将脱口而出的责难。
“王老师问要不要报强化班。”杜澎克制着说。
“不报。”冷冷的话伴随着关门反锁的声音,一同拍在杜澎脸上。
杜澎气哼哼地回到客厅。既然杜如舍不得打,那么承受杜澎的怒火这件事,就非常自然地落到了如氏身上。
“真他妈是个丧门星!”杜澎一脚踹在如氏脸上,把他踹得从地上惊慌地爬起来,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,“给老子舔脚!”
如氏的胃里还翻涌着先前的尿液,他强忍着胃里翻上来的氨骚味,和不断往他鼻腔深处钻的脚臭,一下一下舔着。
开始的半小时,他集中精力,用眼睛盯着杜澎的脚底,分辨哪里的死皮最厚,哪里的脚气最严重,溃烂最深,而刻意用舌尖顶上去,用力舔舐,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杜澎对此很满意,他一只脚搭在如氏头顶,另一只脚被如氏捧在手里,任由如氏舔舐,而他在手机上点开一部短剧,很快沉浸进去。
短剧大概一分钟一集,100集的短剧放完时,如氏的舌头已经完全麻木。他早已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,口水也流干了,只能把累得僵直的舌头搭在嘴唇外面,用脖子带动下巴推挤着它,像用搓澡巾一样搓在杜澎的脚底。
而等到第二部80集的短剧放完时,如氏连脖子也酸痛得几乎动不了了,他开始觉得晕眩,觉得膝盖要断掉了。但是杜澎没有说停,所以他必须继续。他微微弯曲撑着上身的手臂,配合腰腹的肌肉,让整个上身来回挪移,带动头部运动,进而让脸在脚底摩擦。
到了第三部,长达120集的短剧,终于结束时,时间已经从下午6点来到了晚上11点多。如氏已经接近昏厥,全靠肌肉本能在机械地往复运动,即使杜澎每隔两分钟就要狠狠踹一脚他的脸,他也再无法提起神,或是挤出一丝额外的力气了。
杜澎放下手机,让现实重新扑向他,他怔了一会,对如氏说:“去让妞妞赶紧休息吧。”
如氏木讷地点点头,他爬去杜如的卧室,刚被杜如放进门,就立刻瘫倒在地。
“你清洁过了吗?给我舔舔脚吧。”杜如说。
如氏的舌头、脖子和手臂都僵着,他说不了话,摇不了头,摆不了手势,只能哼哼着在地上扭动两下。
杜如揪着他的耳朵,迫使他跟着她去厕所,被她用牙膏刷了舌头(这是为了防止杜澎的脚气传染给她)。
“求、求,我、不行。”回到卧室后,如氏一字一顿地说。
杜如虽然平时对如氏有些同情和照顾,但她毕竟是一个高中年纪的小女孩,正处于对享受没什么抵抗力的年纪。所以她无情地拒绝了如氏的请求,只一味地催促他舌头快点动起来,甚至用写完了墨的中性笔芯戳刺他的肩膀。
如氏赖在地上,死活不肯起来。杜如对于得寸进尺的违抗一向反感,她踩着如氏的脖子,踏到他的脸上,看着他因为口鼻被捂和脖子上的重压而窒息,脸慢慢充血变红,随后逐渐发紫。
“不舔就踩死你。”杜如居高临下地说。
这句玩笑意味居多的话,在急切渴求氧气的如氏耳里,变成了恐怖的威吓。他的女神,此刻变成了处刑的刽子手,宣言着要杀死他。这让他陷入极端的恐慌,他原本僵直的脖子立刻在激素的作用下猛烈点头。
关灯之后,屋内一片漆黑。杜如安逸地躺在舒适的床上,呼吸浅而均匀。她命令如氏跪在床脚,给她舔一夜的脚,这样多少能缓解足部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发黏的不适感。
如氏默默执行着残酷的命令。带着大脑为了应对极致的心理痛苦,而产生的深潭一般的麻木,他的神智收缩成一个无限小的奇点,整个人物化成了一台机械。
他堕入了恒久的绝望。
文/人仿
脖子上的布条勒得很紧。
他跪在玄关的鞋架旁,忐忑地等待着。不久之后就要回家的那一对父女,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,但他必须用最恭敬的方式,迎接他们回家。因为他们是他的主人。
七年前,跑长途货运的杜澎在沿着大车司机们口耳相传的路线,穿过一条村边被大车压烂的破路时,在村里的饭店看到有一个穿着破棉衣的老妇,挨桌问人要不要小男孩续香火。杜澎把老妇叫来细问,得知老妇的老伴早已去世,唯一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一起打工时,工地的电梯坠落导致双双死亡,她没办法再养活手里牵着的孙子,只能找个好人家托付出去。杜澎听完,当场便买下了那个八岁的小男孩。
按理说,凡是买男孩来续香火的人家,都会把买来的孩子视作己出,并让孩子继承本家的姓氏。但杜澎没有这样做,他并不在意所谓的香火,他在意的是他的女儿,杜如。十年前,她的妻子在为她诞下女儿时,难产大出血而死,杜如也因此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。因此,杜澎没有让买下的小男孩随自己的性,甚至没有给他起名,他只是想像旧社会一样,给家里买个伺候人的奴仆,顺便给杜如找个伴,补偿一下她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的伤痛。
这些事情,被亲奶奶卖掉的小男孩都不知道,那时候他还太小,理解不了也记不住这么复杂的事情。他脑海里最早的记忆,是第一次走进杜澎的家门,看到比自己大一岁的,漂亮的杜如姐姐时,心中的油然而生的欢喜和惊叹。
但是这种欢喜没能持续几秒。他记得当时,杜如叉着腰,高傲地跟他说,以后要管她叫“小主”,管杜澎叫“主子”。对于一个一直在农村生活,没有上过学,也没有看过电视的小男孩,是无法自主理解杜如从电视剧里看来的那些词汇是什么含义的,他只能木讷地点点头,心头的惊喜慢慢变成疑惑。
因为杜澎不让他姓杜,所以杜如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,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他做姓氏,从此他就顶着“如氏”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,开始了当牛做马的家奴生活。时间流转,到现在,杜如已经从小女孩变成了高二的青春少女,而如氏则在阴阳不良和长期饥饿中长成了瘦骨嶙峋的15岁少年。
轻快的脚步声打断了如氏的思绪,他连忙端正姿势,神思流过身上的每块肌肉、每个关节,确定它们输出了适量的力道,弯折成了规定的角度,这样才能维持最标准的伏地跪姿。但他其实有些过度担心,因为这跪姿是杜澎一点点用皮带“教”出来的,早已经刻进他的肌肉记忆,几乎不存在出错的可能。尽管杜澎自己其实是不知道他想要如氏怎么做的,他只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用皮带把如氏抽得皮开肉绽,缩在地上,失神地不断重复求饶的话。这种太监般的跪姿,是如氏一点点摸索出来,能让杜澎心里产生皇帝般的爽感,从而迅速消气的,好用的跪姿。
脚步声越来越近,杜家租的房子位于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事业单位的宿舍楼上,总共只有六层,没有电梯,杜家位于顶层。一般人连续爬到六层的时候,即使腿部肌肉不累,心态上也累了,脚步声往往都会变得沉重而响亮。因此如氏可以通过水泥台阶上传来的不同鞋子、不同力道、不同频率的踩踏声,判断出是谁来了。现在这种像小鹿一般,蜻蜓点水似的细碎快步,是杜如的。
钥匙在门外碰撞,插入锁孔,滞涩地扭转,随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咣啷咣啷地打开了。如氏抬头看去,一瞬间,杜如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,正对上如氏那双唯唯诺诺的,丫鬟般的眼睛。
如氏迅速移开眼神,低下头,看到杜如手里那张,被她用两个指尖轻巧地捏着的试卷。虽然卷面上的汉字他几乎完全看不懂,只能勉强地认出几个(还不确定有没有认错),但是上面的数字他是看得懂的——102,比之前拿回来的卷子上面的数字要低一些。
“啊,这是这次补习班模拟测验的卷子。”杜如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,眼神里有些害羞,也有些歉意。
如氏点点头。他其实不明白模拟测验到底是个什么概念,但从杜如的反应里,他能看出,这张画着各种符号的纸,和以前那些长得差不多的纸一样,都会让杜澎烦躁,从而给自己带来苦难,是颇为不详的东西。因此,出于对主人的话做出即时反应的义务,他只是点了点头,但并不能说出什么话来。
“你不用跟着伺候我了,”杜如转身往卧室走去,“你还是跪着等着迎接那个人吧,这样他回来心情好点儿,还能少骂我两句。”
随后,如氏卧室里响起书包被扔在床上的噗的声响,随后是电扇开关的喀哒声。时值七月中旬,北方进入雷阵雨多发的时节,积蓄了两天的厚重雨云笼罩着小城,水汽填满了空气分子的每一个缝隙,天候又闷又热,涨红了脸,憋着劲儿要来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骤雨。
家里并非没有空调,只是房东鸡贼地将空调另设了一个电表,收取额外的电费,因此杜澎和杜如都舍不得开,只一人有一个小电扇。如氏跪在门口,不知是汗还是潮气凝结成的水珠挂满了他的全身,周围静滞的空气压得他喘不上气,他听着杜如卧室里电扇的嗡嗡声,想象着那股风如果吹在自己身上,会是如何的畅快。
一阵突如其来的紧张感紧急中断了如氏的幻想。那是一种超前于意识和思考的恐慌,是身体在捕捉到最细微的线索时,来不及通知大脑,而先行让身体进入应激状态的脊髓反射。有人将这种机制称为直觉,也有人将这种感受认定是第六感,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。总之,在恐慌袭来的几百毫秒之后,如氏才弄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他听到了杜澎上楼的脚步声。
他的额头死死压在地面上,连呼吸和心跳都凝滞了。世界变得一片寂静,各种嘈杂的声音全部退潮般地离他远去,只有杜澎的脚步声,离他越来越近。
咚,咚,咚——
“贱奴给爸爸请安。”门推开的一瞬间,他重重磕头。
如氏口中所谓的“爸爸”,并非指的杜澎,而是指的杜澎的脚。这个“认足作父”的点子,是杜澎在听到同行轮班的司机,说起“有个外围为了挽回一个富二代竟然认富二代的狗做爹”的猎奇新闻时,忽然想到的。
直到杜澎坚硬的皮鞋底踩住他的后脑,如氏才停下来。他叼住皮鞋的后跟,一边含糊不清地念叨着“贱奴给爸爸更衣”,一边用嘴褪下鞋子。
一丝肉眼可见的白雾从皮鞋和脚的缝隙间蒸腾出来,那是长途出车,吃睡都在车上,连续三四天不曾脱鞋,而从脚底分泌出来,经过反复闷蒸、浓缩出的脚汗蒸汽,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的显现。浓重的恶臭逸散到空气中,被如氏吸入鼻腔,像强酸一样立刻腐蚀了他的嗅觉神经。极其浓郁的咸臭甚至让他感到一种浓重的苦涩,仿佛鼻腔和气管都被脚汗蒸汽夺取了水分,开始皱缩、枯萎。
“回来了?”杜如从卧室里钻出来,淡淡地打招呼。
“他妈的,今天卸货的时候手滑了一下,被接货的老板扣了五十卸货费。”杜澎一边骂,一边脚下发力,把如氏的头狠狠踩进鞋窝。
从四面八方,洪水似的涌来的臭味,立刻让如氏全身的肌肉都不自觉抽搐起来。即使嗅觉中枢立刻在恶臭中近乎麻痹,但杜澎作为多年的脚气患者,那种真菌发酵所产生的,超越嗅觉的,反人类的味道,直接侵染到他的骨髓、他的灵魂里,让他像被水淹没,快要淹死的人一样渴求新鲜的氧气。
杜澎没有在意如氏激烈的反应,他隔着袜子,把发痒的脚底踩在如氏留着寸头的头上,在脑上那些坚硬的发茬上摩擦。茁壮的发茬被迫穿透袜子纤维的缝隙,刮挠、戳刺着令人发痒的死皮,和恶心的溃烂处,让杜澎感到一阵舒适。
杜如皱了皱鼻子,退了两步,借口去摆碗筷,迈着小碎步溜去厨房里了。
“行了,一会吃饭的时候再好好伺候你爸爸。现在先给我把衣服换了。”杜澎命令道。
换完衣服,杜如已经摆好了碗筷。父女两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小的餐桌两侧,桌上挨挨挤挤地放着两副碗筷,以及杜澎买回来的吃食:两盒路边三轮车小摊上买的快餐炒菜,几个馒头,一小塑料袋炸花生米,以及一提罐装啤酒。桌下则是跪着的如氏,他艰难找着角度,用牙齿轻轻啃食杜澎脚底的死皮和腐肉,缓解他脚底的瘙痒。
“这几天都不出车吗?”杜如看着啤酒问, 平淡的语气仿佛她和杜澎只是同事关系。
“最近活儿少。”杜澎只是简单地回答。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脚底,如氏那湿润柔软的舌头和略显尖锐的牙齿,交替给他带来的轻抚和解痒的舒爽感受。
两个人都没再说话,客厅里一片寂静,只有杜澎的脚底板上,如氏用舌头像犁地一样来回刮蹭,用牙齿像锄头开垦一样地啃食,所发出的沙沙的声音。
过了二十分钟,直到如氏的舌头和咬肌都开始酸痛,桌上只剩下一点残留的菜汤,和两个被当成烟灰缸的空啤酒罐子,杜如才犹犹豫豫地开口,说:“模拟考的成绩下来了。”
“多少分?”
“反正是够本科了。”
“我问你多少分!”杜澎提高音量,他的脚趾狠狠抠紧如氏的脸,如氏感觉自己的五官都要被从脸上挖下来了。
“102……”杜如小声说。
“怎么又下降了!以前不是能考130的吗!”
“这次考的是高三难度的题!算了,跟你说了你也不懂!”杜如一撑桌子,站起来,大步走回自己的房间,砰地关上门。
“你!”杜澎起身,刚想去追,电话却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,随即坐了回去,抄起电话接通:“哎,王老师——”
他对着手机,满口答应,脸上都跟着不自地对着空气流露出紧张而讨好的笑容,也顾不上使用脚下的如氏了,只是僵僵地坐着,好像魂被吸到了电话的另一边。
“哎,哎,好的王老师,我理解,咱们都是为了孩子的成绩。您让我再考虑一下,后天孩子过去上课的时候,让她跟您说要不要报强化班。”
挂断电话,杜澎的脸迅速垮了下去,他烦躁地点开微信,忽略那一堆货运群里的未读消息,直接点开支付界面,看着上面堪堪达到五位数的数字,陷入纠结。
如氏也感受到了杜澎的焦虑,虽然是通过被杜澎踹脸的方式。杜澎沾满他口水的脚底,直直地踹在他的脸上,带着一股发泄的力道,几乎要把他的脸皮从骨头上搓下去。他被踹得东倒西歪,在地上栽倒又爬起,一遍遍重新跪到杜澎脚下,无言地履行着沙包的职责。
他宁愿自己多受点苦,也不愿意杜澎把气撒在杜如的身上。他已经形同枯槁,浑身布满了各种类型的伤疤,再承受多一些痛苦也无所谓。可是杜如,他的小主,她的身体是那样的富有青春活力,焕发着即将成年的少女特有地光彩。那吹弹可破的细腻皮肤,如何经得起杜澎的粗糙有力的大手的拍打?那小鹿一般的纯洁活泼的心灵,又如何经得起杜澎毫无文化,满口粗鄙之语的责骂?
杜澎从哈德门烟盒中抽出一支新的点上,猛吸了一口,一脚将如氏踹了个趔趄:“去把东西收拾了,然后把妞妞给我叫过来。”
如氏跪直,把空的泡沫盒子和啤酒罐等垃圾扫到垃圾袋里,叼着前往厨房扔掉。由于父女两个都不会做饭,也没时间学,因此厨房几乎未曾使用过,成了如氏的狗窝,兼堆放杂物的地方。在厨房,如氏举起快餐盒,喝掉了里面的菜汤。杜澎是不会买如氏的食物的,他对如氏的思路还停留在农村养狗的阶段,即给狗吃点人的剩饭就行了,没有剩饭就饿着。因此,如氏每天就只能靠菜汤里的油星补充一些能量。杜如上高中后,如氏的境遇才好一点,因为杜如会好心地托名减肥,给他剩几口馒头米饭,或是假装吃到了花椒或骨头渣子,吐出一口嚼碎的菜或肉留给他。
因此,如氏是十分喜欢杜如的,在他封闭的,全部面积只有60平米的世界里,杜如就是他的天使,他的女神。他爬到杜如的卧室门前,虔诚地叩首,轻声呼唤着“小主”。杜如还在赌气,房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,如氏只能听到客厅传来杜澎外放看短视频,隔几秒就会传来一次的猴子笑声。
直到如氏听着杜澎又抽完了两根烟(他通过两次打火机的声音判断的),他才终于听到门后面,啪嗒啪嗒向他走来的拖鞋声。
“干什么?”门缝里露出杜如的黑色猫猫拖鞋,她水润的脚趾蜷缩在鞋尖,白皙得刺眼。
“主子请您去客厅。”如氏卑微地伏在地上。
门打开了,他的头被柔软的拖鞋底狠狠踹了一脚,随后门又重重地关上。
如氏只能颤抖着爬回杜澎脚边,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杜澎的表情,恐惧地陷入对自己会遭到什么惩罚的猜想中。杜澎一手拿着手机,一手抓着如氏的头发,不由分说的把他的脸拽到自己裆下。那是他要撒尿的意思。
杜澎对排泄是没什么羞耻心的,他在长途货运的过程中,经常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排泄,不知被路过的司机和路人看过多少次了。他喜欢生殖器露在风中撒尿的感觉,但他更喜欢把它插进如氏的口腔,在温润柔软的包裹中一泻千里,顺便还能欣赏如氏强忍干呕的痛苦表情。所以他毫无羞耻地脱下裤子,往如氏胃里灌了一泡充满啤酒的代谢产物的,腥臊的浓尿。
浓重的骚味瞬间激发了如氏的生物本能,他的胃立刻就猛烈收缩起来,他的身体自然地想要抵抗入侵的污物,把尿液排出体外,但他的大脑却下达着相反的命令。在违抗天性的对抗中,如氏的五官扭曲成一团,腹部一凹一凹地向内抽搐,坚持了半分钟,才终于等到杜澎尿完,瘫在地上干呕着喘着粗气。
提上裤子,杜澎踩过如氏的腹部,大步走向杜如的房门,握起拳头猛砸。
“干什么!”杜如一把拉开门,站在门口和杜澎对峙。
杜澎的拳头举起又放下。无论再怎么生气,他也是没法对女儿下手的,他觉得亡妻的在天之灵还在注视着他,要他做一个好父亲。最终,他嗫嚅了几下,还是忍住了即将脱口而出的责难。
“王老师问要不要报强化班。”杜澎克制着说。
“不报。”冷冷的话伴随着关门反锁的声音,一同拍在杜澎脸上。
杜澎气哼哼地回到客厅。既然杜如舍不得打,那么承受杜澎的怒火这件事,就非常自然地落到了如氏身上。
“真他妈是个丧门星!”杜澎一脚踹在如氏脸上,把他踹得从地上惊慌地爬起来,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,“给老子舔脚!”
如氏的胃里还翻涌着先前的尿液,他强忍着胃里翻上来的氨骚味,和不断往他鼻腔深处钻的脚臭,一下一下舔着。
开始的半小时,他集中精力,用眼睛盯着杜澎的脚底,分辨哪里的死皮最厚,哪里的脚气最严重,溃烂最深,而刻意用舌尖顶上去,用力舔舐,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杜澎对此很满意,他一只脚搭在如氏头顶,另一只脚被如氏捧在手里,任由如氏舔舐,而他在手机上点开一部短剧,很快沉浸进去。
短剧大概一分钟一集,100集的短剧放完时,如氏的舌头已经完全麻木。他早已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,口水也流干了,只能把累得僵直的舌头搭在嘴唇外面,用脖子带动下巴推挤着它,像用搓澡巾一样搓在杜澎的脚底。
而等到第二部80集的短剧放完时,如氏连脖子也酸痛得几乎动不了了,他开始觉得晕眩,觉得膝盖要断掉了。但是杜澎没有说停,所以他必须继续。他微微弯曲撑着上身的手臂,配合腰腹的肌肉,让整个上身来回挪移,带动头部运动,进而让脸在脚底摩擦。
到了第三部,长达120集的短剧,终于结束时,时间已经从下午6点来到了晚上11点多。如氏已经接近昏厥,全靠肌肉本能在机械地往复运动,即使杜澎每隔两分钟就要狠狠踹一脚他的脸,他也再无法提起神,或是挤出一丝额外的力气了。
杜澎放下手机,让现实重新扑向他,他怔了一会,对如氏说:“去让妞妞赶紧休息吧。”
如氏木讷地点点头,他爬去杜如的卧室,刚被杜如放进门,就立刻瘫倒在地。
“你清洁过了吗?给我舔舔脚吧。”杜如说。
如氏的舌头、脖子和手臂都僵着,他说不了话,摇不了头,摆不了手势,只能哼哼着在地上扭动两下。
杜如揪着他的耳朵,迫使他跟着她去厕所,被她用牙膏刷了舌头(这是为了防止杜澎的脚气传染给她)。
“求、求,我、不行。”回到卧室后,如氏一字一顿地说。
杜如虽然平时对如氏有些同情和照顾,但她毕竟是一个高中年纪的小女孩,正处于对享受没什么抵抗力的年纪。所以她无情地拒绝了如氏的请求,只一味地催促他舌头快点动起来,甚至用写完了墨的中性笔芯戳刺他的肩膀。
如氏赖在地上,死活不肯起来。杜如对于得寸进尺的违抗一向反感,她踩着如氏的脖子,踏到他的脸上,看着他因为口鼻被捂和脖子上的重压而窒息,脸慢慢充血变红,随后逐渐发紫。
“不舔就踩死你。”杜如居高临下地说。
这句玩笑意味居多的话,在急切渴求氧气的如氏耳里,变成了恐怖的威吓。他的女神,此刻变成了处刑的刽子手,宣言着要杀死他。这让他陷入极端的恐慌,他原本僵直的脖子立刻在激素的作用下猛烈点头。
关灯之后,屋内一片漆黑。杜如安逸地躺在舒适的床上,呼吸浅而均匀。她命令如氏跪在床脚,给她舔一夜的脚,这样多少能缓解足部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发黏的不适感。
如氏默默执行着残酷的命令。带着大脑为了应对极致的心理痛苦,而产生的深潭一般的麻木,他的神智收缩成一个无限小的奇点,整个人物化成了一台机械。
他堕入了恒久的绝望。
好耶!
支持人仿佬